Table of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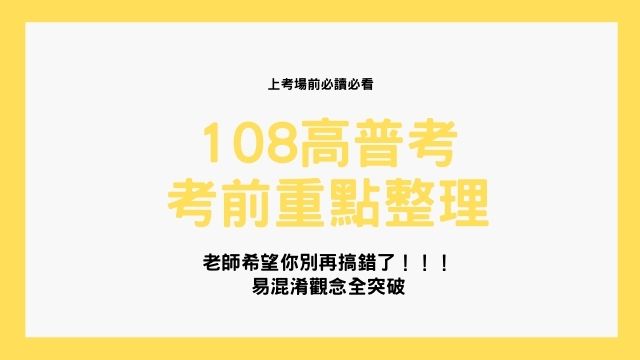
不用擔心一般行政刑法(含概要)如何準備,常考考點、易錯題目,這邊都幫你做了篩選和彙整囉!題題皆附上詳細解析,同學們最容易搞混的觀念全部都幫你打通~考前高效總複習這樣做就對了!
【刑法(含概要)】(108高普考考前重點整理)
名師私房話
「刑法」此科,向來為考生於國家考試中,一較高下之科目;其理由在於,公法性質之刑法,每每涉及人權議題,往往爭議性高,亦造成學派間論點分歧、異說者眾。從立於國家考試的角度而論,建議應考者,應該具備以下正確觀念:
一、由「傳統考點分析」之角度,刑法體系重在邏輯思考:
刑法經過數個世紀之演進,已經形成完整之思考邏輯體系;所以,於本科之準備上,更重要的是結合學說與判例,了解該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了何種犯罪?並依照刑法犯罪三階論的格式,從通說之角度以為判斷。
二、面對「近期修法」之新、舊法衝突,應將困難學理,化成精簡口訣:
由於多數同學對於刑法,都是陌生的,更遑論遇到「刑法大修正時期」之應對方式建立!是故,建議應考者,應以
「將困難學理化成精簡口訣」之準備方式,以期自己能有一個簡單且易記的開始,以免發生「上考場前身影案牘勞形、上考場後腦筋空空如也」之憾事,並能藉此自信地、跨出愉悅的第一步!
三、以「實務見解特色」觀之,最好之應答方式,即是觀摩師資架構答法、以勝過自我盲目練習:
畢竟,老師就實務意見,總是較為熟悉;應考者只要跟隨課堂老師之答題訓練,以為學習解題技巧,即足應付國家考試。
Q1.刑法總則中,對於公務員之定義及認定。
刑法上就公務員之認定:
我國舊刑法第10條第2項就公務員之規定中,為:「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然而,舊刑法第10條第2項有關公務員之定義,其規定極為抽象、模糊,於具體適用上,經常造成不合理現象,例如:公營事業機構,其從事於該公司職務之人員,應認為係刑法上之公務員。然何以同屬股份有限公司,而卻因政府股權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或未滿之不同,使其從事於公司職務之人員,有刑法上公務員與非刑法上公務員之別?實難以理解。
公務員在刑法上所扮演之角色,有時為犯罪之主體,有時為犯罪之客體,為避免因具有公務員身分,未區別其從事職務之種類,即課予刑事責任而有不當擴大刑罰權之情形,故宜針對公務性質檢討修正。
新刑法第10條第2項就稱公務員之認定,改謂下列人員: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新刑法之認定,依據刑法上之角度,審認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為「公共事務」之實行,而不再以人事行政上之觀點認定,應屬可採。是故,依據題意,行為人(旅客)甲因不滿列車長乙要求補票,而痛扁乙成傷。甲是否成立妨害公務罪?爭點如下:
肯定說:
例如法務部57年刑一字第7821號函示內容:公營事業之職員亦為刑法上之公務員,其在火車上執行查票之行為自可認為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行為,以強暴脅迫妨害查票行為者,自應成立本罪。實務早期見解多採本說。
雖為私法關係營造物,如鐵路局者,因鐵路法第71條訂有對於「拒絕查票者,得處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之規定,故鐵路局之列車長在行使相關職務時,將成為公務員。臺北市捷運局人員依大眾捷運法規定,亦有相同情形。
否定說:
例如司法院70年廳刑一字第253號函示:妨害公務罪屬侵害國家權力之罪,公務員必也依據法令執行公法上之行為,始具實行國家權力之性質,亦因此際公務員之地位特殊,而有特加保護其執行行為之必要。苟若所執行者為私法上之行為,則國家係與該私法行為之相對人立於相對等之法律地位,並非實行國家權力之屬,縱對執行該行為之公務員施以強暴脅迫,亦不構成妨害公務罪。
再者,司法院73年廳刑一字第603號函亦認為:臺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雖係公營機關,但其班車行車人員係執行私法上之營業行為,並非公權力之行使,乘客對之如有施暴毆打成傷,僅屬刑法傷害罪之範疇,不成立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
綜上所述:
新刑法之認定,既然依據刑法上之角度,審認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為「公共事務」之實行,而不再以人事行政上之觀點認定。
Q2.古典犯罪理論體系、新古典體系及目的犯罪論體系有何不同?試申論之。
刑法上所謂犯罪,乃行為人基於主觀上之惡性,而反映於客觀上之不法行為是。理論上,學者間見解互異,扼要言之,大致有如下三次演進內涵:
古典體系:
所謂古典學派之古典理論,學者約有貝林、貝加利亞、李斯特等人,基於罪刑法定主義之遵守,故構成要件乃一決定刑罰之根據及界限,它是客觀、描述、中立及無色彩的,行為人之行為一旦符合構成要件之描述,且不具阻卻違法事由之時,即該當於不法行為。
所差異者,乃行為人主觀上之心態,其心理要素僅是影響罪責,而不涉及不法行為。
新古典體系:
由於古典學派的過分注重客觀不法行為之描述認定,並未考量行為人該等行為目的、傾向等之價值判斷,學者梅耶認應出此等增設,使構成要件不再單純,中立無色彩;違法性之方面,亦承認法益衡量下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概念。
至於責任,則為心理及規範之要素。
新古典暨目的論綜合體系:
時至近代,尤以20世紀後段,在學者韋伯、韋爾采等之戮力下,犯罪理論結構益趨成熟,構成要件不再是客觀審認已足,而應包含行為人主觀上認知與意欲之要素,以為區分故意或過失,違法性則採最有利於行為人之阻卻方式。
至於罪責(責任)部分尤其精采,更應符合違法性認識與期待可能性之要求。
Q3.對於客觀歸責理論的內涵及功能,我國學說上至今有何相同或相異的看法?
客觀歸責理論之意義:
所謂客觀歸責理論,希望透過歸屬風險之概念,確立並限制犯罪因果的成立條件和範圍,用行為對法益受害結果具有法律上重要的風險,解釋行為人之意志支配的可能性。
客觀歸責理論的初衷,是以客觀歸責為主軸,重新架構犯罪行為的階層體系,亦即重新建立統一的歸責理論,並且是以行為的客觀面作為歸責的基礎和重心。
本理論在學理上持相同看法如下:
本論之基礎,在於行為人之行為製造不被容許之風險,並且這個風險在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結果上實現,並且這個危險也導致某一結果的發生;但是,假如這種危險與結果間之關係,不是構成要件的效力所掌握的範圍,那麼,結果的發生仍然不可歸責於危險行為。
本論可適時、合理說明因果範圍之限縮,用以排除刑事責任之歸屬;特別在過失犯之審查中,用以取代傳統「注意義務與否」之抽象判斷,使得犯罪審查時,儘早於前階段中排除。
不過,本論在學理上所持相異(爭議)看法如下:
客觀歸責理論試著分離「因果」及「歸責」之兩種概念,藉以改革傳統條件論;不過,條件理論之修正改革方向,似乎足以說明歸責範圍之限縮,易言之,本論並不需要。
「容許之風險」最實用之下位論,即為信賴原則,藉以解釋行為人交通上之正確行為。然而,此即傳統上行為人是否合法遵守注意義務之審查,此為同論,毋需另外以風險之容許與否解釋之。
本論最爭議處,在於其破壞了傳統既有犯罪論之三階審查;例如:過失犯中,本來應該為「主觀」無預見迴避可能之要素,但卻逕於「客觀」中不被歸責,如此,主、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失去各別審核之價值。
Q4.主張正當防衛,以現有不法之侵害行為,及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條件。正當防衛之成立,侵害行為是否以作為為限,抑不作為亦包括在內?防衛行為是否以故意行為為限,抑過失行為亦有可能?
正當防衛之意義:
正當防衛又稱為緊急防衛,乃就現在所發生之不法侵害或攻擊行為,在無法立即獲得公權保護之危急情狀下,基於人類自衛本能,主觀上自為客觀必要之防衛。此為刑法保護法益之精神相符,係刑法規範所允許之一種權利行為,而構成緊急防衛權,排除行為之違法性,不成立犯罪。
正當防衛之成立,其侵害行為是否包含不作為?
肯定說:正當防衛僅以有現在不法侵害為必要,即足成立防衛行為。不作為,無論係純正或不純正不作為均對結果之侵害具有原因力,可發生侵害,防衛者只要無忍受義務,即足為正當防衛之對象(侵害),不限於積極行為之必要。
否定說:單純之不作為對現狀無顯著之變更,如債務不履行及純正不作為犯等,對之無正當防衛可言,若以強制力迫其二者行作為義務,應以自助行為論。
通說:採肯定說,如對無故滯留他人住宅內受退去之要求而不退去者,以實力迫其退去(純正不作為犯之不作為)是。
正當防衛之成立,其侵害行為是否包含過失?目前通說亦承認之,其情狀可細分如下:
行為人若在有「防衛意思」之前提下:
防衛意思,乃行為人認識現有不法侵害存在之單純狀態。因而,基此防衛認識說之主張,防衛意思與過失,即有同時並存之可能性。易言之,過失行為,亦有成立正當防衛之可能。
例如:甲見乙持刀逐步逼近,乃拔槍警告其勿再前進,惟因極度驚恐,以致誤觸扳機,將乙射殺身亡。
甲見乙持刀逐步逼近,係認識現有不法侵害之存在,嗣拔槍警告其勿再前進,已具有防衛意思存在。其拔槍警告之行為,雖係故意行為,但並無扣動扳機之意思,旋因極度驚恐,以致誤觸扳機。
其誤觸扳機之過失行為,嚴格言之,並非因防衛而直接實施之行為,惟係對應於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意思所實施防衛行為之延長線上的行為,仍得認其屬於防衛行為之一部分。
因此,甲主觀上既有防衛之意思,客觀上亦有防衛之行為,自得主張正當防衛。
反之,若行為人倘對於此客觀情狀無所認識,自應否定正當防衛之成立。
例如:甲近日甫自某處購入黑星手槍一把,深夜於客廳賞玩之際,不慎誤觸扳機,子彈正好打中隱於牆角暗處,正舉槍瞄準,擬將甲射殺之仇人乙,致乙不治身亡。
乙正舉槍擬將甲射殺,為現在不法之侵害,係屬正當防衛之客觀情狀。甲對此客觀情狀,並無任何認識,亦無任何對應之意思,不能認為有防衛意思存在,自無防衛行為之可言,甲應負過失致死罪責。
Q5.甲一人獨居,因寒流來襲,在家打算借酒取暖後就寢。不久已至酒醉,未料竟有竊賊闖入,甲因飲酒過量,除制服竊賊外,更持木棍將竊賊打死。甲應負何刑責?
依題意所示,甲將竊賊打死可能為「自醉行為」,而非「原因自由行為」。茲將兩者分別論述如下:
原因自由行為之意義:
所謂原因自由行為,乃行為人於完全責任能力之狀態時,即有實現特定犯罪之意思,或能預見特定法益之侵害,因而使自己陷於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狀態,且在此狀態下實現犯罪。
易言之,行為人之侵害法益行為,雖為行為人一時喪失責任能力狀態中所為之舉動;然行為人所以陷於無責任能力狀態,乃出於行為人可得自由決定者,此即為「原因自由行為」,或「可控制之原因行為」。
然而,與原因自由行為相當近似,但我國刑法卻無予區別者,即為「自醉行為」:
自醉行為之意義:
由於「原因自由行為」必須於原因行為階段時,即具有一定法益侵害的故意、或對於一定法益的侵害有預見可能性,才能用故意犯或過失犯的法理加以歸責。
但是,如果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間並無前述兩種情況的關連性,行為人於先行行為時,對於法益的侵害,既無故意、也不具備預見可能性及迴避可能性時,就不能用「原因自由行為」的法理加以掌控。
因為,原因自由行為可罰性的基礎,在於行為人於「原因階段」時有意的要破壞法益,或至少能預見一定法益被破壞的可能性。所以,才能在有一定的法益遭受侵害時,把行為人的責任劃歸到原因設定時。
我國現行刑法中似乎無法明文規範自醉行為:綜上所述,甲之打死竊賊行為即為在醉態行為時方才產生法益侵害,是否可逕依原因自由行為認定?即有疑問。
結論:
若依題意,甲之打死竊賊行為,應以自醉行為認定為是;
然而,於我國實務意見中:
甲之行為仍然將依據我國刑法第19條第3項之原因自由行為規定而論處之,無法因此減免刑事責任。
至於甲之構成要件及其違法性,應論以「因傷致死之加重結果犯」:
因傷部分(故意傷害既遂罪):因正當防衛而主張阻卻違法。
致死部分(過失致死罪):因為防衛過當,不能阻卻違法;但得依據刑法第23條但書,主張減輕其刑。
Q6.甲教唆乙至丙宅將丙殺害,惟乙誤闖丁宅,將丁槍殺後,適丁之妻戊返家撞見,為殺人滅口,乃復將戊槍殺後逃逸。試問甲、乙各應負何刑責?
教唆犯之錯誤理論:
原則上,教唆犯在其所教唆之構成要件範圍內負其責任即足,就逾越之部分及無可預見之情狀下,則依自我負責原則由正犯承擔。
正犯若發生構成要件錯誤時,按我國學界及實務上通說言,教唆犯逕依正犯之刑責予以論處。
正犯若發生違法性錯誤時,除教唆犯顯為利用正犯該錯誤而應成立間接正犯外,餘者正犯僅為刑責之減免,共犯亦同。
本題說明:
正犯乙誤闖丁宅殺之行為:此乃「誤丁為丙」之客體錯誤,因丙、丁均為生命法益相同,故為等價客體錯誤。
乙之等價客體錯誤,為「故意殺人既遂」無影響。
甲為教唆犯,若依傳統之共犯從屬立場而言,則甲應從屬於乙之刑責亦為「教唆(故意)殺人既遂犯」。
正犯乙就戊殺人滅口行為:由於甲並未教唆乙殺害戊,此純屬乙之自我決定,已超出甲之教唆範圍及預見程度,甲毋庸負責。
結論:
就正犯乙先後殺害丁、戊,犯意各別、臨時起意,成立殺人既遂數罪併罰。
甲應負一個教唆(故意)殺人既遂罪之故意犯即足。
Q7.甲趁深夜便利商店員工值班整理貨物之際,欲竊取收銀機內的錢財,正好上門之顧客乙見甲形跡可疑,出言喝止。甲見事跡敗露,準備騎乘門口尚未熄火之自己機車而逃逸。極富正義感之乙向前追捕,擋住甲之機車不讓離去,甲為避免被逮捕,急催油門衝撞乙,乙閃避跌坐地上,甲揚長而去。試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
本題之爭點,可能為刑法分則上第329條之準強盜罪;然而,是否逕論以該罪?似有討論之處。茲分析於下:
刑法分則上之準強盜罪(以下稱本罪):
以我國刑法第329條:「竊盜或搶奪,因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以強暴、脅迫者,以強盜論。」規定觀之可知,若行為人為竊盜或搶奪之著手實行後,為了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而當場施暴;因其施暴之強制手段,與竊盜、搶奪之間,具備時空上緊密關聯;
亦即,行為人不再屬於竊盜或搶奪行為之宵小鼠輩,進而翻身成為暴力相加之惡霸匪徒,是故刑法特別以準強盜罪,以為加重論處。
惟,依據本題題意,甲似乎尚未著手於竊盜行為,即已為施暴之行為:
題中,甲趁深夜便利商店員工值班整理貨物之際,欲竊取收銀機內的錢財,正好上門之顧客乙見甲形跡可疑,出言喝止。無論以實務界習以適用之形式客觀說、抑或學界上之主客、觀混合說而論,甲並未就此動手達成被害財物失竊之密接關聯性、或因動手而提昇被害財物失竊之直接危險性。
準強盜罪之行為人,雖然就本罪(竊盜或搶奪行為)之犯罪階段並不要求必然既遂;但是行為人犯該本罪時,務必要經過「著手竊盜或搶奪行為之實行」方有準強盜罪之思考。
甲並未著手竊取,即準備騎乘門口之自己機車而逃逸;亦即,題中行為人甲「根本未為竊盜或搶奪行為之著手」時,即無準強盜罪之適用、更毋需運用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30號解釋文之內涵文義,以為判斷「被害人是否為難以抗拒」之程度。
甲之刑責:
甲既然於未為竊盜著手而事跡敗露,準備騎乘機車逃逸下,而急催油門衝撞見義勇為之乙,致乙閃避跌坐地上而揚長而去。甲至多僅能考量「故意竊盜預備罪」、「故意傷害既遂罪」、及「強制罪」等罪:
依據罪刑法定主義,我國刑法並不處罰故意竊盜之預備犯;是故就此部分無法論處。
至於「甲為避免被逮捕,急催油門衝撞乙,乙閃避跌坐地上」之行為部分:
由於我國刑法就故意傷害既遂罪採「實害犯」之認定,應該就個案上審查乙是否因閃避跌坐地上而受到實質傷害程度,以為認定甲之刑責。
是故,若乙僅為跌坐地上而已、未有任何受傷之實害時,甲可能無故意傷害罪之刑責。
惟,甲為避免被逮捕,急催油門衝撞乙;甲顯然意圖逃逸,而以強暴脅迫方法,將見義勇為之乙撞倒,妨害其行使正當防衛之權利,甲之該等行為,顯屬「手段目的關聯性」之不法,是故,甲仍應成立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
Q8.試說明枉法裁判罪、與濫權追訴處罰罪之不同。
刑法第124條之枉法裁判罪:
現行刑法第124條規定:「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判或仲裁者,處……。」即為所謂「枉法裁判罪」。
本罪之行為:枉法裁判或仲裁:
所謂「枉法裁判」,指明知法律而故為出入者;如依條文之法定本刑僅有徒刑、拘役而減為罰金、以及無加重事由而故予以加重均屬之。
至於枉法裁判或仲裁之結果,究對受判決人生利或不利之可能,尚非所問。
行為人須有故意:須明知法律而有故為出入裁判仲裁之故意。亦即,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須法官有枉法裁判之故意,始可成立,若單純因法律見解不同,則非本罪該當。
刑法第125條之濫權追訴處罰罪:
本罪之行為主體:
有追訴或處罰職務之公務員:本罪行為人為「有追訴或處罰犯罪職務之公務員」,故前者指檢察官,後者指法官。
警察是否為行為主體:至於警察(包括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若其行為該當於本罪構成要件,因行為主體資格不符,僅能構成傷害或妨害自由,再依刑法第134條而加重其刑爾。
本罪之行為:
濫用職權為逮捕或羈押:所謂濫用職權,必先有其職權,方有濫用之餘地;若無此權,則為妨害自由罪。例如:警察濫行羈押人民,應論以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罪,而依第134條論處。
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本款須有強暴脅迫之行為手段,倘依詐術、利誘或其他方法,即於本罪之要件不符。
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無故不使其受追訴或處罰。
本罪之加重結果犯:本條第2項乃規定,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時之處罰,為刑法總則之加重結果犯。
刑法第124條之枉法裁判罪與刑法第125條之濫權追訴處罰罪之異同:
前罪之行為主體,為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故司法審判官、軍法審判官、行政法院法官及商務仲裁人,均屬本罪適格之主體。倘無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擅為本罪之行為,應適用刑法第128條,論以越權受理訴訟罪,無成立本罪之餘地。而代表國家公權力之行使者:檢察官,因其僅有對犯罪之追訴權,而無審判權,故為後罪之行為主體。
前罪為一般性、原則性規定,故若另有特別法規定,例如:後罪之第1項第3款,應從其特別法規之後罪。亦即,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處罰,或明知為有罪之人而使其不受處罰,後罪之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既有特別規定,應不包括於前罪所謂枉法裁判之內。
Q9.甲拿等重於硬幣十元之電玩代幣予以投入乙經營之自動販賣機「詐騙」飲料一瓶,甲有何刑責?
甲對乙之自動販賣機「詐騙」飲料一瓶之行為,究竟成立刑法上之對機器詐欺罪?還是故意竊盜罪?不無爭議。
刑法上之對機器詐欺罪之意義:
所謂刑法第339條之1第1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依實務上之見解及共識,乃指行為人就該機器設備提供商品或服務所預設之通常收費方法之程式上,施用與該正常使用方法相類似而不當之手法,因而取得不法利益。
是故,甲拿等重於硬幣十元之電玩代幣予以投入乙經營之自動販賣機「詐騙」飲料一瓶,顯然為對該販賣機施用詐術而得利,該當刑法第339條之1之構成要件。
不過,行為人之該等行為,對機器是否可以顯現出詐欺其「判斷能力」之要素?似非無疑:
所謂刑法上的錯誤是指,被騙的人主觀的認知和客觀的事實不一致。機器不會發生認知上的錯誤。理由是,機器只接受指令而有所反應:不正確的指令,機器不會有反應;正確的指令,機器才會有反應。
販賣機所有人的意思,本來就不包括對於使用非真正貨幣者拒絕飲料給付,否則販賣機所有人事先就會在軟體內輸入徹底辨識貨幣所需要的程式了。販賣機所有人最後對販賣機的想法是,只要有和十塊錢(或其他貨幣的組合)等大等重的金屬投進機器,這一部機器就自動把飲料送出來。
小結:因為機器僅有其「感應能力」,根本不具備「判斷能力」;是故,甲用等重於十元之偽幣仍非對機器詐欺,僅能論以竊盜行為,成立故意竊盜既遂罪才是。
綜上論述:
甲既然無所破壞機之「判斷能力」、也非對機器及所有人(老闆)有其身體傷害之機會;是故,於學理中,甲應該當者似為故意竊盜既遂罪,較為妥適。
雖然學理上之意見成理;然而依據罪刑法定主義及實務多數意見,甲仍僅能論以刑法第339條之1之「以不正方法對收費設備詐欺取財得利既遂罪」。
Q10.甲、乙二人應丙之邀共同乘坐由丙所駕駛之小客車,不料途中丙不慎肇事撞傷丁。甲、乙二人思報答丙以往之恩情,而共同商量由甲出面自承該車係由甲所駕駛肇禍。嗣由於丙被訴過失傷害之偵查程序中,甲、乙均供前具結而為虛偽之陳述係甲駕車肇事。甲、乙兩人共犯(或各犯)何罪?
甲之刑責:
甲代丙出面之行為可能構成頂替罪(刑§164Ⅱ):
客觀上言,甲自承自己是肇事者,依實務與學說見解,頂替行為僅以行為人頂替犯罪事實即可,不以實際頂名為要件,故甲的行為客觀構成要件該當。
主觀上言,甲對上述頂替行為有認識並決意為之,具備頂替故意,且係為使事實上違犯刑法的丙隱匿或使之隱避,具備藏匿人犯之意圖,主觀構成要件該當。
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刑法頂替罪(刑§164Ⅱ)。
甲供前具結為虛偽陳述之行為,可能構成偽證罪(刑§168):
客觀上言,甲係於偵查程序中,以證人身分,供前具結,陳述甲係肇事之行為人,足以影響偵查結果,並且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該當。
主觀上言,甲對上述事實有認識並決意為之,具備偽證故意。
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甲構成刑法偽證罪。
乙之刑責:
乙於偵查程序中虛偽陳述並具結,其行為可能構成刑法頂替罪(刑§164Ⅱ)。
按頂替罪之性質為己手犯,所謂己手犯者,係指該必由行為人親自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因此,於己手犯之概念下即無共同正犯之成立餘地。
乙並不與甲共同頂替丙,是故乙本身並未實行頂替行為,因此客觀構成要件不該當。是故,乙不成立本罪。
乙於偵查程序中虛偽陳述並具結,其行為可能構成刑法頂替罪之幫助犯(刑§164Ⅱ、§30):
乙客觀上對甲有幫助行為,於偵查程序中,供稱甲為肇事之人,且乙主觀上亦具有幫助故意,構成要件該當。
乙主觀上對其行為有知與欲,具備故意,該當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
乙未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且有責,故成立本罪。
乙於偵查程序中虛偽陳述並具結,其行為可能構成刑法偽證罪(刑§168):
乙於偵查程序中,就於案情有關係之重要事項為虛偽之陳述,該當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
乙主觀上對其行為有認識與意欱,具備故意,該當本罪之主觀構成要件。
乙未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且有責,故成立本罪。
甲、乙之罪數競合:
甲成立刑法頂替罪及偽證罪,且為一行為犯之,基於兩罪法益相異(前者為破壞真實犯罪行為人之被追訴權;後者為破壞司法權之公正行使),應論以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偽證罪處斷。
乙成立刑法頂替罪之幫助犯及偽證罪之正犯,並為一行為犯之,論以想像競合,從一重之偽證罪處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