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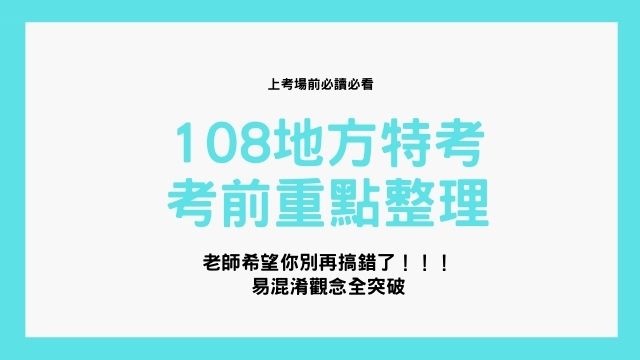
不用擔心地方特考法制法廉刑事訴訟法如何準備,常考考點、易錯題目,這邊都幫你做了篩選和彙整囉!題題皆附上詳細解析,同學們最容易搞混的觀念全部都幫你打通~考前高效總複習這樣做就對了!
【刑事訴訟法】(108地方特考考前重點整理)
Q1、刑事訴訟法增修電子監控防逃機制(法務部108.07.03新聞稿)
【重點】: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本(108)年7月3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建構我國電子監控防逃機制新里程碑。
鑑於近年來一再發生社會矚目之刑事案件被告逃亡,嚴重傷害司法威信,行政院於108年5月27日治安會報指示,應積極從制度面設法防堵刑事被告利用交保到判決定讞期間之空窗期逃匿,以維國家司法公信。
經檢視現行制度,除法院依法羈押被告外,過去以警調人員隨行監控之防逃方式不僅欠缺法律明確規定,而且耗費人力、物力,實際亦難有效防阻被告逃匿,故經本部與司法院多次研商後,共同研擬刑事訴訟法有關防逃機制修正草案,再經…整合各方不同意見後,提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蒙立法院之重視與支持,於今日三讀修正通過。
此次刑事訴訟法防逃機制,增訂多種羈押替代處分,明文授權法官、檢察官得命被告遵守包括: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例如電子腳鐐)、居家監禁、交付護照及旅行文件、禁止處分特定財產等羈押替代處分,且得視被告遵守情形,為變更、延長或撤銷;另明訂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於裁判法院送交卷宗前執行,杜絕逃亡之空窗期;同時亦規定被告經法院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逾二年有期徒刑,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者,檢察官得逕行拘提。
從而,未來偵審程序中,檢察官或法官於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時,得審酌被告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定相當期間,命被告接受適當之科技設備監控,藉由科技化的嚴密監控,隨時掌握被告行蹤,使有逃亡之虞之被告,杜絕逃亡念頭,而順利到案執行。
本次修法兼顧國家刑罰權之實現與人權之保障,強化現行刑事訴訟法羈押替代處分與相關裁判執行制度,俾刑事司法系統得依個案情節,適時啟動防範被告逃匿機制。本部未來將與司法院共同落實並完善相關執行之細節措施,以有效防止被告逃匿,確保國家刑罰權之實現。
Q2、警方於取得通訊監察書後,即依法對涉及毒品犯罪之甲進行電話監聽。未料監聽過程中,另外聽到甲曾竊取轎車的通話內容。試問,此一內容可否作為法院日後認定甲犯竊盜罪之證據?
【重點】:
監聽處分之意義:
在刑事訴訟法的強制處分行為中,所謂監聽處分,即通訊監察權,乃為國家司法機關干預、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強制處分,故其發動與實施,應符合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的調和,不可任意為之。
至於通訊監察之核准及實施,究竟應具備何種正當程序之基本要求,所取得之證據,方具證據之適格,除如前述,應以憲法比例原則作為審酌之基礎外,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定,尚須遵守重罪原則、相關性原則、書面許可原則、一定期間原則、監聽事後書面通知原則、及監察對象特定原則等精神。
本案在偵查程序中,以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毒品案罪嫌」而聲請監聽,然事實上卻意外監聽甲「另為竊盜犯行」之他案。
按監聽之重罪原則,係以法定刑度及列舉罪名,惟本件係竊盜罪嫌,係違反重罪原則。
原則上,此部分監聽超出原來核定之罪名範圍,屬「他案監聽」、或稱「另案監聽」,因與本案監聽係屬附帶監聽而得之不同對象,且非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所列之重大犯罪,並未重新聲請監聽,故本應無證據能力。
然而:
此「另案監聽」所取得之證據,如若係執行監聽之司法機關,自始即虛偽以本案監聽之罪名(涉嫌毒品案罪嫌)、而聲請核發通訊監察書,利用於其監聽過程中發現另案之證據(另為竊盜犯行)者;因該監聽自始即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且執行機關之違法取證惡性重大,依據新修正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本文:「依第五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執行通訊監察,取得其他案件之內容者,不得作為證據。……」之規定,則其所取得之監聽資料及其所衍生之證據,不得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
反之,倘若屬於本案依法定程序監聽中,偶然獲得之另案證據:
基於與「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善意容許之例外」規範、以及新修正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但書:「……但於發現後七日內補行陳報法院,並經法院審查認可該案件與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具有關連性或為第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罪者,不在此限。」規定觀之,倘若另案監聽亦屬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得受監察之犯罪,或雖非該條項所列舉之犯罪,但與本案即通訊監察書所記載之罪名有關聯性者,自應容許將該「另案監聽」所偶然獲得之資料作為另案之證據使用。
結論:警方既然合法取得通訊監察書後,即依法對涉及毒品犯罪之甲進行電話監聽,並於合法監聽過程中,偶然獲得甲竊取轎車的通話內容,此一內容自可作為認定甲竊盜罪行之證據。
Q3、試就大法官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說明警察臨檢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
發動臨檢的門檻與發動刑事訴訟搜索、扣押、逮捕有何不同?
臨檢與「逮捕」、「留置」有何不同?
【重點】: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作成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文,以為說明警察臨檢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此號解釋文意義重大,除了促成警察職權行使法之制定,也釐定警方依法行政與刑事偵查之分際。
先就其基本精神予以說明:
臨檢之意義: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可知,臨檢行為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其實施之手段為:臨場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等。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該等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藉由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以達到維護治安之目的。是故,臨檢應注意時間、地點及對象,不得任意臨檢、取締或隨機檢查、盤查。重點如下: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臨檢進行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之身分。
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
發動臨檢的門檻與發動刑事訴訟搜索、扣押、逮捕行為之差異:發動臨檢的門檻與發動刑事訴訟搜索、扣押、逮捕之行為當屬不同,因前者為行政處分,而後者為司法之強制處分。按現行刑事訴訟法就搜索、扣押、逮捕之強制處分要件,簡述如下:
搜索行為:
搜索之發動,不論是對被告搜索時,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二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搜索時,應具備「必要時」之要件。若是對第三人為搜索,該條第二項規定應具「有相當理由」之程度。
或許條文上之「必要時」或「有相當理由」有模糊不夠精準之處;不過都強調了強制處分權發動之門檻,需要有相當之理由以為支持。以美國實務上言,所謂相當之理由(Probable Cause),即指應負舉證責任及宣誓擔保之佐證(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除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一條不要式搜索外,此處所言之舉證,不需該證據之證明力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只需有此可能即可,且為客觀情狀之認定為足。此即所謂自由的證明主義。
扣押行為: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之規定以觀,只要犯罪偵查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發現刑事訴訟法第一三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物品,均得扣押之。
依上該條文規定之精神,可見扣押行為應在強制處分行為發動後,在發現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時,方可扣押之,而非任意依犯罪偵查機關任意違法執行之。
逮捕行為:依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規定,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利害關係人亦得請求檢察官、司法警察官逮捕之。
臨檢:
依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一條第三款:「臨檢: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路段,由服勤人員擔任臨場檢查或路檢,執行取締、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規定以觀,臨檢亦屬警察執行勤務方式之一種。
臨檢實施之手段:檢查、路檢、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均屬對人或物之查驗、干預,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人民之有犯罪嫌疑而須以搜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手段者,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一二八條、第一二八條之一,其僅屬維持公共秩序、防止危害發生為目的之臨檢,立法者當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是故臨檢之發動至少亦應有法律之依據,並符合必要性原則始可(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35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臨檢與「逮捕」、「留置」之不同:
所謂臨檢,依前所述,僅為行政上之行政處分,是故僅能短暫地於臨檢場所對於當事人做基本之人別詢問或隨身物品之檢查。
就此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文認為:「臨檢應於現場實施,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安寧者,不得要求其同行至警察局、所進行盤查。其因發現違法事實,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身分一經查明,即應任其離去,不得稽延。」即為此義。
至於「逮捕」或「留置」依前述可知其為司法上之強制處分,本屬限制當事人之人身自由,以為順利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留置亦同,乃為對於因受逮捕、拘提或主動到案之當事人,為明白案情拘束其身體自由於一定之處所而言。故彼等本為拘束人身之強制處分權,一切均應依照刑事訴訟法之規範,以為保障人權。
Q4、詳附理由解答下列問題:
起訴之方式,有所謂之「卷證併送制」與「卷證不併送制」兩種,其分別之意義為何?兩者最大之區別為何?
在理論上,起訴方式採卷證不併送制後,對於偵查、起訴與審判等階段之訴訟程序運作得以達成何種效果?
【重點】:
卷證併送制與卷證不併送制之意義、區別:
卷證併送制:所謂卷證併送,乃基於職權主義之精神,就檢察官於起訴時,應將其偵查程序中所得之卷宗、證物,一併送交法院審查。
卷證不併送制:亦即國內傳統通說中常言之起訴狀一本主義(起訴書一張主義),其指檢察官起訴時,僅能將起訴狀送交於法院審方,至於其他相關證據、書狀則留待審判程序進行中予以提出攻防。
基本上,「卷證併送制」與「卷證不併送制」其區別在於其刑事訴訟基礎理論。依目前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三項:「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規定可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係採職權主義,其起訴之方式,採卷證併送制度:
在職權主義刑事訴訟制度下,訴訟之進行、證據之調查,於起訴後屬法院之職權,為尊重審判程序進行,檢察官應將偵查所得之證據、書狀一併移送於法院。法官於審理前即可充分進入審判之準備程序,進而對判決時完全掌握訴訟理由,如未能事先準備,恐難盡充分調查證據之義務,是故有採本制度之必要。
當事人主義之制度,其論據乃源自英美法中「兩造平等」精神。法庭審方於審判程序前,應尊重雙方對等之精神,不應對任一方有先入為主,亦不應受任何證據窺視之影響。故檢察官起訴時,除起訴書外,不應併予提出偵查所得之相關事證,以確保審判者不預先產生對被告不利之偏頗,進而損及被告之權益。
卷證不併送制對偵查、起訴及審判程序之影響:
於偵查中,應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法官間接知悉本案之相關事證。
於起訴中,必然需要「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訴因制度」以為配合,使被告便於防禦。
於審判中,由於被告遭追訴時,除被告資料、犯罪事實及罪名外,其餘事證皆未詳載,故原告檢方務需就其犯罪事實盡其力為描述,而達到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至於法院,則必然踐行直接言詞審理主義,及傳聞法則之遵守,落實公判集中審理制度之精神,以為心證新鮮性之維持。
Q5、試說明審判程序中,共同被告審判上之合併及分離。
【重點】:
共同被告為合併審判:
其理由在於:訴訟經濟、避免判決矛盾或量刑不公、協助發現真實、避免被告間懷疑審判法院執法不公。
反之,如合併審判已造成「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而有保護被告權利之必要」時,法院自「應」分離審判;惟有時合併審判對共同被告之一人不利,但是尚未達到「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而有保護被告權利之必要」之程度,法院「得」裁量分離審判。
共同被告為分離審判:
分離審判之理由:
法院認為適當時(裁量分離)。
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而有保護被告權利之必要者(必要分離):
共同被告之利害相反。
被告權利因合併審判而受影響。
有其必要性。
分離審判時所受之權利保障:
例如,甲與乙涉嫌共同殺人,甲於警詢或偵訊程序中一再強調,人是乙殺的、與自己(甲)並無關係。
本案若檢察官將甲、乙合併起訴,法院對甲、乙:
若為合併審判時,甲亦為同一審理庭中之被告,乙不得請求法院將甲以「證人」身分而傳喚作證。
反之,若為分離審判時,則在就乙為審判庭中,甲之身分為乙案中之證人,乙可以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一、第159條之二等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乙得請求法院將甲以「證人」身分而傳喚作證,以為對質詰問。如此對乙較為有利時,法院應該為甲、乙之分離審判。
Q6、甲正在路上騎車,與另兩名騎士乙、丙擦撞(責任在乙、丙),甲基於正當防衛推開乙、丙導致該兩人受傷。不料警察巡邏經過,看到甲打人,案經乙、丙提出傷害告訴,警員將甲以故意傷害罪移送地檢署。檢察官偵訊時,只依甲動手打人予以偵辦,根本不再進一步偵查甲是否為正當防衛而阻卻違法。最後,檢察官向甲表示,如甲願意:「賠償乙、丙各五萬元、遵守三年緩起訴的觀察期」,將可給甲就該案緩起訴的機會。試問:
如此緩起訴處分是否合法?
這種緩起訴處分不當之處究竟為何?
如此緩起訴處分和「無罪推定」法則有無衝突?
【重點】:
該緩起訴處分仍然合法:
民國九十一年元月修法,對刑事訴訟法最大衝擊之處,莫過於檢察官「緩起訴處分職權」之增訂,檢方將擁有「起訴猶豫權限」,透過對非重罪毋庸全舉,配合各種矯治配套措施,使得被告有「不受法院審理、仍能矯治改正」之機會,以減少被告受審之機率,亦能使法院減輕案源之壓力,使檢方充分篩檢案件,對檢察官權限而言,不得不謂大增。
適用案件:依新法第253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僅適用於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適用標準: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253-1Ⅰ)。
是故,本小題檢方之緩起訴處分雖然對行為人非常不利,但是檢察官之處分仍然合乎法律規定。
這種緩起訴處分不當之處:
未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緩起訴之撤銷,係檢察官依職權或告訴人之聲請而為,未予被告適當之抗辯機會。
檢方若有如此大之裁量權限,不但抽象,範圍過大,將來必遭批評。
一味強調檢方擁有之預防功能,將流於起訴法定原則之形式,並非要當。
被告雖已完成負擔或指示,卻仍須承受緩起訴撤銷之不利益,而於撤銷後,又不返還被告所履行之負擔,其法律效果確係過於嚴厲。
緩起訴處分和無罪推定法則有程序上的衝突:
緩起訴處分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的重心是訴訟程序在法院進行,嫌犯因此就處在一種衝突的情境。亦即,即使嫌犯可以阻卻違法而不罰,但是在緩起訴中卻還要接受檢察官所諭知的負擔,以免除行為人所將要面對的審判上痛苦。實際上,這反而使行為人得到莫需有的處分。
喪失就犯罪成立與否驗證之可能:緩起訴處分由於欠缺正式的訴訟程序,因而喪失對犯罪構成要件詳細驗證的可能性,實務上可能因為主客觀構成要件的證明困難,形成緩起訴的動機。此種不起訴處分的方式,非但限縮了人民接受正式審判的權利,同時也使得被害人被排除於正式程序之外,而損及訴訟權的利益。
Q7、何謂偵查不公開原則?其目的為何?刑事訴訟法有何相關規定?
【重點】:
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其目的:
刑事訴訟,乃國家基於公權力,就特定人之特定犯罪事實,適用抽象之刑事法規,以形成並確定其具體刑罰權是。所謂特定人及特定犯罪事實,以實體法言,稱為行為主體及犯罪行為;以程序法言,稱為被告及犯罪事實。其承辦之機關包含法院及代表國家公權力之檢察機關,各自代表追訴及審判機關。
是故在刑事訴訟之意義上,乃有廣、狹二義(釋字第392號解釋文):廣義刑事訴訟係指以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為目的之有關行為,包括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四程序;而狹義刑事訴訟乃專指確定國家刑罰之有無及其範圍為目的之起訴與審判程序,即僅以法院、原告、被告三者相互間所發生的法律關係為範圍之訴訟行為。
是故,「檢察官」負起偵查程序且充當公權行為之原告,在「不告不理(不訴不理)」之精神下,檢方一方面負責控制法院案源,另一方面監督行政系統辦理維護治安(即警察機關)之權限,責任相當重大!檢察官於偵查中,應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透露偵查方向、法官間接知悉本案之相關事證、並保護當事人嫌犯的名譽。反之,於起訴後,必然需要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訴因制度以為配合,使被告便於防禦。
相關規定:
例如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28條之規定:
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
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231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另外,從本法第33條:「辯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Ⅰ)。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之影本。但筆錄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Ⅱ)。」之反面解釋觀之,基於偵查不公開,偵查中並不允許辯護人閱卷。
Q8、檢察官對於被告為緩起訴處分,告訴人如果不服,可以循何種途徑尋求救濟?試根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分析之。
【重點】:
檢察官對於被告為緩起訴處分時,告訴人如果不服,可以依循救濟途徑如下:
再議程序:
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規定:「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第253條、第253條之1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得聲請再議。」此即再議制度。
易言之,緩起訴處分並非一經檢察官處分即告確定,針對緩起訴本身,得依不起訴處分之不服途徑,也就是再議程序救濟。
檢察官製作緩起訴處分時應製作處分書敘述處分之理由,以正本送達於告訴人、告發人、被告及辯護人(§255ⅠⅡ)。
有告訴人之案件,除其曾同意緩起訴者外,告訴人得於收受緩起訴處分書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首長聲請再議(§256Ⅰ),處理程序如同一般的不起訴處分的再議程序(§257、§258)。
反之,「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直接通知告發人。」
交付審判程序之聲請: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緩起訴處分依新法的做法,允許其交付審判,新法將緩起訴處分納入得聲請交付審判的範圍。
據此,告訴人於不服上級法院檢察首長駁回再議之處分者(§258),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Q9、起訴之被告為A,審判中B冒A之名到案受審;法院未察,率行辯論終結,而為A有罪之判決。問:此項判決對於A與B之效力各如何?應如何補救?試分別說明之。
【重點】:
本題乃涉及訴訟客體之錯誤。蓋因被告及犯罪事實構成案件之內涵,若案件之審理內容卻與檢察官起訴內容有誤時,效力何在?效果何屬?不無疑問。說明如下:
起訴之主體(觀)效力:依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66條:「起訴之效力,不及於檢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之規定,乃限定審判之對象,以經起訴者為限,不及於其他共犯。至於何謂檢察官所指被告,在學說上約為如下爭議:
意思說:以檢察官之主觀意思說為準,何人為被告,以檢察官之意思認定之。檢察官欲對甲為訴追,甲雖冒乙之名,但被告仍為甲而非乙。
表示說:本說認為,何人為被告,應參酌檢察官之意思及其他情事(如起訴書所載之事實,被告之人別資料)加以判斷,而非以起訴書所載之姓名為唯一判斷標準。故有稱之為實質表示說者。
行動說:本說主張刑事訴訟之被告,其認定標準,應以實際上以被告地位,而為訴訟行為或受訴訟行為之人為準。
國內學者有採所謂的表示說與行動說之「併用說」或「折衷說」者,亦即原則上以表示說為主,在例外情形,以行動說為輔。
本題中乃冒名頂替之審判效力問題:所謂冒名頂替,乃指被告以外之人冒用被告名義到案,例如本題明明起訴之被告為,審判中卻冒之名到案受審,此時應依發現之時點判斷如下:
於第一審發現時,因尚未判決,可將被告本人拘捕到案,而為裁定更正;並另就冒名頂替者另行移送偵辦。
於第二審發現時,因為有判決存在,依實務見解,應將原判決撤銷,另為判決。第三審發現者,應撤銷原判決,以裁定發回第一審判決。
如果判決確定後始發現,此時,因被告始終未出庭受審,應認為原判決違背法令,宜提起非常上訴撤銷之,重新進行審判。
本題,遭起訴者為審判中冒之名到庭受審,法院未察,率行審判,並為有罪之判決。此一判決有瑕疵,應分別其發現之時點,而為不同救濟。至於本非被告,但亦未於本案中列名被告而為起訴,故本案起訴之效力本不及之;但之行為已涉及觸犯刑法第164條第2項之頂替罪,應為另行偵辦。
Q10、何謂拘捕前置主義,其立法目的為何?並就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試述之。
【重點】:
拘捕前置主義之意義:
由於羈押為最嚴重侵犯人權之強制處分,是故「必要性原則」、「比例性原則」為最高指導目標。
偵查中之犯罪嫌疑人既然僅受偵查而非定罪,是故檢、警機關對其應循一定程序依法漸進(傳喚、拘提、逮捕、羈押);若司法人員未能依法為之而對嫌犯為逕行聲押,不免傷害其權利甚鉅。
是故,本法規定若干條文,以告知檢、警機關一個重要觀念:「合法拘、捕」是為羈押處分之前提要件,否則即應釋放嫌犯。
拘提逮捕前置主義之相關規定:
檢察官若遇有羈押之情形卻未經聲請者,應即將被告釋放。但如認有第101條第一項或第101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如不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而有必要情形者,仍得聲請法院羈押之(§93Ⅲ)。
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101條第一項各款或第101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押之。第93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用之(§228Ⅳ)。
前項司法警察官,應將偵查之結果,移送該管檢察官;如接受被拘提或逮捕之犯罪嫌疑人,除有特別規定外,應解送該管檢察官。但檢察官命其解送者,應即解送(§229Ⅱ)。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經拘提或逮捕者,不得解送(§229Ⅲ)。
Q11、甲經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乙以普通竊盜罪起訴。審理中,法官丙發現甲係夜間侵入住宅行竊。檢察官乙隨即追加起訴甲無故侵入住宅罪。試問該追加起訴是否合法?
【重點】:
訴之追加起訴之意義:
目的:訴之追加,係利用舊訴之程序而提起,以符訴訟經濟之要件。
要件:
須本案之訴未經撤回。
須於本案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如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仍許追加起訴,對本案訴訟程序並無實益,故不許於辯論終結後為之。
追加者為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7)或本罪之誣告罪。
方法(種類):
被告之追加。
犯罪事實之追加。
利用舊訴之程序提起,故新舊訴須行同一訴訟程序。
本題「夜間侵入住宅」與「竊盜」之間乃刑法上之加重竊盜罪,本即為一罪,非為相牽連案件(數罪)。
是故檢察官僅就其一部起訴者,法院依本法第267條得全部加以審判, 毋庸適用第265條之規定,即第265條與單一案件無關(必為數罪數案件之情形始有追加之問題)。
故檢方再予追加起訴乃不合法。
Q12、私人採證及私人指證(指認)究可否為證據?
【重點】:
私人採證:
原則上,近代法治國對證據排除(禁止)使用之精神,乃來自於限制國家機關濫用公權採證之基礎;但是,若違法採證之程序乃來自「私人」,應如何討論?
國家保護義務說:將私人採證程序看成「違法採證者對被害人之法益侵害」,國家有義務保護該被害人。
證據能力概括規定說:法官仍應依刑訴法第155條第2項,以審查該採證者是否在個案上侵害被害人之(自主性)基本權限。
法條依據說:尋找法條之規範以求非法採證者是否構成犯罪:
若有(如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等相關法令):則為「非法」採證,不可採之。
反之,若採證者之行為阻卻構成要件該當或阻卻違法,則其採證行為非為違法,其證據仍可採為使用。
實務意見亦從法條依據關係上以為解釋:
刑事訴訟法上「證據排除法則」,係指將有證據價值或真實之證據,因取得證據之違法,而予以排除之法則。而私人之錄音、錄影之行為所取得之證據,應受刑法第315條之1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範,私人違反此規範所取得之證據,固應予排除。
惟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之規定:「監察者為通訊之一方或已得通訊之一方事先同意,而非出於不法之目的者,不罰。」通訊之一方非出於不法之目的之錄音,所取得之證據,即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
私人指認:
私人指認之意義:
所謂私人指證,乃被害人或證人向司法人員作對被告的指認;在傳統實務工作中,常見警方找來一群(甚至於只有一名)狀似嫌犯的人們排成一列、或提出數張(甚至於只有一張)長相可疑、兇惡、猥褻的人頭照片;這些照片可能年代久遠、可能模糊不清,警方此時卻以該等人群或照片要求被害人或證人作指認,一旦被害人或證人有些許認定時,司法人員即鎖定目標開始發動刑事訴訟程序。
私人指指認之程序:
就此種習以為常的「私人指認」程序,我國刑事訴訟法並無許可與否的相關規範;但是,這種程序攸關被指認人的權益,最高法院近年來已有所表態,值得注意;綜合最高法院及相關學說意見,在程序上,「私人指認」應符合下列標準:
禁止司法人員預先設定嫌犯,而應由指認人先行陳述嫌疑人的特徵,再令被害人或證人指認。
禁止誘導被害人或證人指認。
禁止一對一、是非式的指認,而應為「列隊指認」(Line-up)。
除該經指認所得之證據外,應需要其他補強證據,以補強其指認之證明力。
Q13、再審與非常上訴之主要區別何在?聲請再審與提起非常上訴之要件為何?兩者判決之效力有何不同?試分別說明之。
【重點】:
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其與非常上訴之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者有異。茲就兩者之主要區別列述如下:
請求主體不同:非常上訴非由最高法院檢察總長不得提起(§441);再審之聲請權人則不以此為限(§427、§428)。
管轄法院不同:非常上訴由最高法院管轄(§441);再審之管轄法院則為判決之原審法院,例外為第二審法院(§426)。
理由不同:非常上訴係以該案件之審判違背法令為理由;再審則以列舉的事實錯誤之情形為理由,且因係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或不利益而有不同(§420~§422)。
對象不同:非常上訴以確定判決、實體裁定及訴訟程序為對象;再審之對象則以確定判決為主。
程式不同:提起非常上訴應以非常上訴書敘述理由提出於最高法院為之(§443);聲請再審則應以再審書狀敘述理由,附具原判決之繕本及證據,提出於管轄法院為之(§429)。
程序不同:非常上訴之判決,不經言詞辯論為之(§444);再審則應先為聲請是否適法之審理,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後,再依法院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433~§436)。
有無期間限制之不同:聲請再審原則上無時間限制,但有例外(§424、§425);非常上訴則無任何時間限制。
聲請再審與提起非常上訴之要件:
聲請再審之要件:
具備本法第四二○條至第四二二條所定再審理由。
由有聲請權人為之(§427、§428)。
遵守聲請再審之期限(§424、§425)。
具備程式要件(§429)。
向管轄法院為之(§426)。
提起非常上訴之要件:
以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為其理由。
由最高法院檢察總長始得提起。
具備程式要件(§443)。
向最高法院提起。
再審判決與非常上訴判決效力之不同:
再審判決之效力一律及於被告經再審判決後,原確定判決視為撤銷,自不生執行之問題。
非常上訴判決之效力,原則上不及於被告(§448);原判決違背法令者,撤銷其違法部分,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者,撤銷其程序,均僅形式上宣告其違背法令,原判決均屬存在,固不生改判之作用;但若原判決之違背法令不利於被告,應就該案件另行判決,若原判決係誤認為無審判權而不受理或其他有維持被告審級利益之必要者,得撤銷原判決,由原審更為審判,其效力則例外地及於被告,即其有現實之效力。
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至對個案之被告予以具體救濟,僅係其附隨之效果,此與因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錯誤而設之再審救濟制度迥然不同,於此,非常上訴,應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核原判決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卷內證據資料觀察,其適用法則並無違誤,即難指為違法,至於事實之認定,乃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非常上訴審無從過問。
Q14、某甲駕駛計程車不慎,撞倒由乙駕駛後座搭載某丙之機車,致某乙與某丙均受輕傷,某乙告訴某甲過失傷害,經起訴並判決某甲無罪確定後,某丙又告訴某甲過失傷害,並由檢察官向同一法院提起公訴,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理由安在?試請詳述之。
【重點】:
依題意,甲之撞擊乙、丙行為,為想像競合犯:某甲駕車撞傷乙及丙,係一行為觸犯兩輕傷罪,即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為裁判上一罪,於訴訟上為同一案件,既經被害人乙提出告訴,檢察官提起公訴獲判無罪確定,該無罪確定判決發生實質確定力(既判力),就此犯罪事實不得再成為訴訟客體。
惟想像競合犯之既判力,效力是否及於全部?頗有爭議,易言之,丙是否可再告訴,而使檢方就此再為起訴?
否定說(實務界採之,如最高法院67年第10次刑庭決議):某甲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其觸犯之數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均屬相同,且係以一行為犯之,依據一行為僅應受一次審判之原則,其應否受刑事制裁,已因前一確定判決所為無罪之諭知而確定,此與連續犯之數行為及牽連犯有方法結果之情形不同,不容再為其他有罪或無罪之實體判決,是對於後起訴者,參照本院二十八年滬上字第四十三號判例及司法院院字第二二七一號解釋,應為免訴判決,如仍為有罪之判決確定者,其判決顯屬違法。若就連續犯、牽連犯有數行為之情形而論,固無不合,但本例想像競合犯僅有一行為,其情形顯有不同。
肯定說(即效力不及全部、丙可再告訴、檢方可再起訴):
想像競合犯乃裁判上一罪(刑§55),雖係一行為,而其所犯者本質為數罪,其效力所以及於全部者,僅係由於從一重處斷之結果。
想像競合犯侵害之法益各別。
結論:目前通說,乃採實務見解,故丙不可再告訴,檢方自不可再行起訴;否則,法院應諭知為免訴判決。
Q15、附帶民事訴訟
【重點】:
意義
指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附帶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回復其損害之請。
當事人
附帶民事訴訟之訴訟主體,固亦為當事人及法院。但當事人中之原告及被告,未必就是刑事訴訟中之原告當事人或被告當事人。茲分述其訴訟主體如下:
原告(§487):犯罪而受有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故凡因刑事訴訟中之被告犯罪,以致權益直接有損害,依民法具有損害賠償求權者,便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作為附帶民事訴訟之原告當事人。
被告:附帶提起民事訴訟,係對於刑事訴訟之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故刑事訴訟中之被告及依民法應負賠償責任之人,例如民法第一八七條之法定代理人及民法第一八八條之僱用人等,其縱非刑事訴訟中之被告,仍均得為附帶民事訴訟之被告當事人。
提起期間(§488)
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
提起程式(§492、§495Ⅰ)
以訴狀或言詞為之。
管轄(以刑事訴訟為標準)(§489)
依本法之事務管轄及土地管轄定之。
法院就本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至第十條為合併審判及指定或移轉管轄之裁定者,視為就附帶民事訴訟有同一之裁定。
就刑事訴訟諭知管轄錯誤及移送該案件者應併就附帶民事訴訟為同一諭知。
訴訟程序
附帶民事訴訟除本編有特別規定外,準用關於刑事訴訟之規定。但經移送或發回、發交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490)。
審判
刑事訴訟之審判期日,得傳喚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及關係人(§494)。
附帶民事訴訟之審理,應於審理刑事訴訟後行之。但審判長如認為適當者,亦得同時調查(§496)。
檢察官於附帶民事訴訟之審判,毋庸參與(§497)。因附帶民事訴訟,純為保障私權而設。
當事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或到庭不為辯論者,得不待其陳述而為判決,其未受許可而退庭者,亦同(§498)。
就刑事訴訟所調查之證據,視為就附帶民事訴訟亦經調查(§499Ⅰ)。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為依據,故法律有此明文規定,惟對於賠償範圍與金額,仍應為必要之調查。
調查證據時,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或代理人得陳述意見(§499Ⅱ),乃使其有提供有利事實及證據,並為辯論之機會。
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但本於捨棄而判決者,不在此限(§500)。
附帶民事訴訟,應與刑事訴訟同時判決(§501)。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如先於刑事訴訟為判決,其事實認定,即失依據。所謂同時判決,其判決書仍應分別製作,不得合為一判決書,不言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