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 of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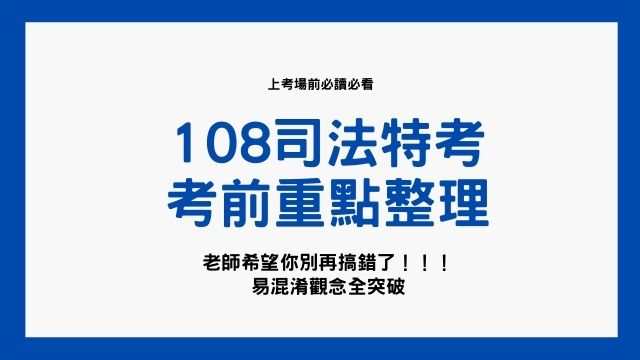
不用擔心司法特考刑事訴訟法概要如何準備,常考考點、易錯題目,這邊都幫你做了篩選和彙整囉!題題皆附上詳細解析,同學們最容易搞混的觀念全部都幫你打通~考前高效總複習這樣做就對了!
【刑事訴訟法概要】(108司法特考重點整理)
★重點引言
刑事訴訟法這一門考科中,實務見解在國考的出題上,一向是非常重要,甚至以往曾經將實務見解直接轉換成考題,因而導致看過實務見解的同學可以輕鬆拿到高分,但沒看過的同學則慘遭毒手,因此這次考前猜題,主要是針對近年重要的實務見解,配合相關學說,以主題的方式進行整理,例如實質辯護、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被告之品格證據等。
另外,有關GPS偵查部分,因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的做成,導致在學說及實務界引起軒然大波,學者爭相寫文章表示看法,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考前務必再次複習相關概念。
最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通聯記錄調取的增訂,從修法已來即爭議不斷,尤其有關通信使用者資料的調取,更是爭議之所在,然而實務見解於日前曾做出重要見解,且不同於以往法務部的解釋,因此更是在國考前不可不知的重要資訊。
一、實質辯護之重要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561號判決:刑事辯護制度係為保護被告之利益,藉由辯護人之專業介入,以充實被告防禦權及彌補被告法律知識之落差,使國家機關與被告實力差距得以適度調節,促成交互辯證之實體發現,期由法院公平審判,確保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而設;辯護人基於為被告利益及一定公益之角色功能,自應本乎職業倫理探究案情,盡其忠實辯護誠信執行職務之義務。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七款規定「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此所謂未經辯護人到庭辯護,依辯護制度之所由設,除指未經辯護人到庭外,尚包括辯護人雖經到庭而未盡其忠實辯護之義務在內。本件上訴人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一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屬於應用辯護人之強制辯護案件,上訴人委任余○○律師為辯護人,於九十六年九月五日審判期日,余○○律師到庭,審判筆錄記載:「選任辯護人余○○律師起稱:為被告辯護,辯護意旨詳如刑事準備書狀所載」等語。然稽之案內資料,上開準備書狀僅止於表明聲請傳喚證人○○,乃準備程序期日應行處理之事項(參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一項),辯護人於原審審判長調查證據後,並未就法律上或事實上意見為上訴人盡其忠實辯護之義務,此與辯護人雖經到庭而未置一詞辯護者無異,原審逕予審判,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819號判決:刑事被告於各審級有受律師實質、有效協助之權利,其內涵應包括國家機關不得否定被告有此項權利,國家機關不得干涉辯護人的重要辯護活動,以及辯護人應提供有效之協助,以確保被告辯護倚賴權應有的功能,並應排除辯護人利益衝突之情形。是否為無效之律師協助,除應由被告具體指出辯護人之辯護行為有瑕疵,致未發揮辯護人應有的功能外,必也該瑕疵行為嚴重至審判已不公平,審判結果亦因而不可信,亦即同時具備「行為瑕疵」與「結果不利」二要件,始足當之。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209號判決:故司法警察(官)明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已表明需選任辯護人,自應待其辯護人到場後,即刻訊問,不得無故拖延。如司法警察(官)待犯罪嫌疑人所選任之辯護人到場後,卻刻意拖延,不遵守應即時詢問之規定,而於其辯護人離去後,始加詢問,使犯罪嫌疑人未獲辯護人之諮商及協助,自有礙於其防禦權之充分行使。此種情形,較之於詢問之初未告知得選任辯護人,尤為嚴重;且既屬明知而有意為之,自屬惡意。因此,依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司法警察(官)以此方法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即時詢問之規定時;其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不利供述證據,難認有證據能力。
二、有令狀搜索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必要時得搜索之」,此所謂「住宅」,應包括人日常居住,與生活起居有密切關聯之一切場所,而附屬於住宅之儲藏室,應視為住宅之一部分,持對住宅之搜索票而於附屬之儲藏室進行搜索,要屬合法,因此所扣押之證據,自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判決: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犯罪證據之物件。搜索以及其後所為之拘捕或扣押等處分,係對於被搜索人之身體、住宅或財產等基本權之強制干預,故而發動實施搜索處分時應謹守法律設定之要件限制。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於九十年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同年七月一日施行。不論新舊法,該條第一項均規定,「搜索,應用搜索票」,揭示令狀搜索之原則;同條第二項則明文列舉搜索票法定必要之應記載事項。其於修正前,應記載事項為「一、應搜索之被告或應扣押之物。二、應加搜索之處所、身體或物件。」修正後,規定應記載「一、案由。二、應搜索之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扣押之物。但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三、應加搜索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四、有效期間,逾期不得執行搜索及搜索後應將搜索票交還之意旨。」並就令狀搜索改採法官保留原則,於第三項修正規定「搜索票,由法官簽名」,及增訂搜索票之得記載事項。此據以規範搜索票之應記載事項者,即所謂「概括搜索票禁止原則」。其中尤以搜索票上之「應扣押物」以及「應搜索處所等」之任何一項,必須事先加以合理的具體特定與明示,方符明確界定搜索之對象與範圍之要求,以避免搜索扣押被濫用,而違反一般性搜索之禁止原則。所謂應扣押之物,指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參照),不以於「有事實足認其存有者」為限,尚包括「一般經驗法則、邏輯演繹或歸納可得推衍其存有者」(如以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之光碟燒錄重製類型為例,其應扣押之物,可記載為「與侵害著作權有關之光碟片、燒錄機、電腦、標籤、說明書、包裝等證物」)。搜索票應記載之事項如失之空泛,或祇為概括性之記載,違反合理明確性之要求,其應受如何之法律評價,是否導致搜索所得之證據不具證據能力之效果,則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之四之規定,視個案情節而為權衡審酌以資判斷之。本件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同年三月十日執行搜索之搜索票上,有關應扣押之物均僅記載「有關違反商標、著作權法等不法證物」。核其記載失之空泛,是否已符合理明確性之要求,尚非無疑。
三、無令狀搜索
對第三人附帶搜索
陳運財師認為對於在拘捕現場之第三人,由於其與被拘捕之人之隱私權益主體不同,附帶搜索所定對於被拘捕人之附帶搜索範圍,自不及於在場之第三人。但如有明顯事證足認該第三人與本案被拘捕之人具有共犯關係,或於拘捕過程中,第三人有藏匿或湮滅關係被拘捕人涉案證據之行為,始可對第三人實施附帶搜索。
逕行搜索於拘捕人犯後,仍否繼續搜索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062號判決: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除有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或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或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等情形,得無搜索票,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外,前述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均應用搜索票,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即明。又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或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等情形,而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者,其搜索之目的在於發現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被拘提之人,故不能為發現應扣押物而為搜索,僅得於搜索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應被拘提之人的過程中,發現應扣押之物時,予以扣押,且於發現應被逮捕或拘提之人後,即應停止搜索,否則,其搜索即屬違法;另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之情形,而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者,其搜索之主要目的,在於阻止犯罪,故侵入發現無犯罪或犯罪之痕跡,應立即退出,而不得為搜索,如發現犯罪或有犯罪痕跡,雖得逮捕人犯,並搜索其身體及其雙手所及之範圍,扣押因此所得暨眼睛所能見到之應扣押物,但不得為逾越逮捕人犯所必要之搜索,否則,其搜索亦屬違法。
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5653號判決:按被告經通緝後,司法警察(官)得逕行逮捕之,於逮捕通緝之被告時,雖無搜索票,亦得逕行搜索其身體、住宅或其他處所,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然對於身體、住宅之搜索,為嚴重侵犯人民身體自由、居住安寧、隱私及財產權之行為,故執行搜索時,自應遵守刑事訴訟法有關之規定,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始符該法保障人民不受非法及不當搜索之意旨。因之,司法警察(官)於逮捕通緝之被告時,若僅係基於發現通緝被告之目的,而對通緝被告之住所或其他處所逕行搜索之情形,其於發現通緝之被告而將其逮捕後,必須基於執法機關之安全與被逮捕人湮滅隨身證據之急迫考量,始得逕行搜索被告身體,又因其逮捕通緝被告逕行搜索之目的已達,除為確認通緝被告之身分以避免逮捕錯誤,而有調查其身分資料之必要外,不得任意擴大範圍,復對被告所在之住宅及其他處所再為搜索,始符刑事訴訟法保障人民不受非法及不當搜索之意旨。
同意搜索須自願性同意
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而搜索依其程式,可區分為要式搜索與非要式搜索,其中非要式搜索又區分為附帶搜索、同意搜索、緊急搜索,此觀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三十條之一之規定自明,上開各項搜索有其法定要件及程序。其中同意搜索應經受搜索人出於自願性同意,此所謂「自願性」同意,係指同意必須出於同意人之自願,非出自於明示、暗示之強暴、脅迫。法院對於證據取得係出於同意搜索時,自應審查同意之人是否具同意權限,有無將同意意旨記載於筆錄由受搜索人簽名或出具書面表明同意之旨,並應綜合一切情狀包括徵求同意之地點、徵求同意之方式是否自然而非具威脅性、同意者主觀意識之強弱、教育程度、智商、自主之意志是否已為執行搜索之人所屈服等加以審酌,遇有被告抗辯其同意搜索非出於自願性同意時,更應於理由詳述審查之結果,否則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四、GPS偵查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偵查係指偵查機關知有犯罪嫌疑而開始調查,以發現及確定犯罪嫌疑人,並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之刑事程序。而偵查既屬訴訟程序之一環,即須依照法律規定行之。又偵查機關所實施之偵查方法,固有「任意偵查」與「強制偵查」之分,其界限在於偵查手段是否有實質侵害或危害個人權利或利益之處分而定。倘有壓制或違反個人之意思,而侵害憲法所保障重要之法律利益時,即屬「強制偵查」,不以使用有形之強制力者為限,亦即縱使無使用有形之強制手段,仍可能實質侵害或危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而屬於強制偵查。又依強制處分法定原則,強制偵查必須現行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始得為之,倘若法無明文,自不得假借偵查之名,而行侵權之實。查偵查機關非法安裝GPS追蹤器於他人車上,已違反他人意思,而屬於藉由公權力侵害私領域之偵查,且因必然持續而全面地掌握車輛使用人之行蹤,明顯已侵害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自該當於「強制偵查」,故而倘無法律依據,自屬違法而不被允許。…GPS追蹤器之使用,確是檢、警機關進行偵查之工具之一,以後可能會被廣泛運用,而強制處分法定原則,係源自憲法第8條、第23條規定之立憲本旨,亦是調和人權保障與犯罪真實發現之重要法則。有關GPS追蹤器之使用,既是新型之強制偵查,而不屬於現行刑事訴訟法或其特別法所明定容許之強制處分,則為使該強制偵查處分獲得合法性之依據,本院期待立法機關基於強制處分法定原則,能儘速就有關GPS追蹤器使用之要件(如令狀原則)及事後之救濟措施,研議制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及實體真實發現之法律,附此敘明。
林鈺雄師認為對此違法GPS之處分,其法律效果之判斷(亦即有無禁止使用),基於蓄意規避之絕對禁止,法院應禁止使用該證據(亦即無證據能力)。
五、被告之品格證據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判決:被告之前科紀錄等品格證據如與犯罪事實全然無關者,為避免影響職業法官認定事實之心證,該等證據應不得先於犯罪事實之證據而為調查,此乃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增訂第四項規定之所由設。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除非被告主動提出以為抗辯,自亦不容許由檢察官提出被告之品格證據資為證明犯罪事實之方法,俾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惟被告之品格證據,倘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參諸外國立法例(美國聯邦證據法第404條(b))及實務(日本東京高等裁判所2011年3月29日岡本一義放火案件判決),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例如被訴縱火之被告,其先前作案之手法有其特殊性,與本案雷同,檢察官雖不可提出被告以前所犯放火事證以證明其品格不良而推論犯罪,但可容許提出作為係同一人犯案之佐證;又如被告抗辯不知其持有物係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檢察官得提出被告曾因施用甲基安非他命毒品被判刑之紀錄,以證明被告對毒品有所認識。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即屬於犯罪事實調查證據之範疇,依我國刑事訴訟現制採行所謂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六、自白
不當之長期羈押與自白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249號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所指被告因違法羈押所為之自白,不得為證據之規定,係指處於非法羈押狀態下所取得之自白而言。其於合法羈押中之自白,本法並無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設有被告經「不當之長期羈押或被拘禁後」之自白,不認其有證據能力之規定(日本憲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同此規定),自不能為相同之解釋。但因受不當之刺激意志薄弱者,易作自我犧牲之特殊心理狀態,而為自白,其虛偽性之危險較大。故被告如受不當之長期羈押或被拘禁所為自白,其自白是否真實(即憑信性),固應加注意,惟此與自白任意性之判斷,尚屬有別。至於所謂「不當」之長期羈押或拘禁,必須經由個案,審酌偵查之必要性、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等之身心狀況後為判斷,不能單純從期間之長短加以判斷。
無需補強證據之事實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635號判決:所謂補強證據,依判示,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是以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係者,其中對於犯罪構成客觀要件事實乃屬補強證據所必要,則併合處罰之數罪固不論矣,即裁判上一罪(想像競合犯)、包括一罪等,其各個犯罪行為之自白亦均須有補強證據(但論者有謂僅就其從重之犯罪,或主要部分有補強證據為已足),俾免出現架空之犯罪認定。至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如故意、過失、知情、目的犯之目的(意圖),以及犯罪構成事實以外之事實,例如處罰條件、法律上刑罰加重減免原因之事實等,通說認為其於此之自白,則無須補強證據,但得提出反證,主張其此等任意性之自白非事實。
七、勘驗與鑑定
司法警察(官)之即時勘察報告
最高法院96台上5224號判決:法院或檢察官因調查證據及犯罪情形,得實施勘驗,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十二條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勘驗之主體僅限於法院或檢察官。惟案發之初,封鎖犯罪現場及為即時之勘察,乃司法警察(官)調查犯罪必要之手段,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一條,各於第三項增訂賦予司法警察(官)「即時勘察權」,以應調查犯罪之實際需要,並補本法僅規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實施勘驗未將司法警察(官)包括在內之不足。司法警察(官)依上開規定實施犯罪現場之勘察,雖與勘驗之工作本質上無若何區別,然於法院或檢察官實施勘驗時,依同法第二百十九條準用第一百五十條、第二百十四條等規定,賦予保障當事人、辯護人得以在場之機會(即學理上所稱之在場權,有差異者僅檢察官有裁量權),而其勘察、體驗所得結果,應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或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審判期日調查證據行勘驗者)法定程式製作勘驗筆錄,或於審判筆錄記載當庭實施之勘驗經過。法院就該被告案件實施勘驗,具有直接審理之意義,其所製作之勘驗筆錄,應有證據能力;檢察官之勘驗筆錄雖屬傳聞證據性質,乃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稱「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之例外情形而得為證據,該勘驗筆錄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之意旨,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承認其證據能力。至於司法警察(官)因即時勘察犯罪現場所製作之「勘察或現場報告」,為司法警察(官)單方面就現場所見所聞記載之書面報告,屬於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之書面陳述,為傳聞證據,該項報告屬於個案性質,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自不適用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第一款傳聞例外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之立法精神,於證明其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始得為證據之使用,或使該勘察報告之製作者以證人身分於審判中到庭陳述其製作報告之經過及真實,即以賦予被告反對詰問權之機會為要件,而承認其證據能力(至證據證明力如何,乃調查、判斷之另一問題)。
司法警察機關囑託鑑定之鑑定書面
最高法院100台上1134號判決: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之必要,雖非不得囑託為鑑定,然此之鑑定並非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之選任、囑託而為,當無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之適用,自亦不該當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所定得為證據之「法律有規定」之例外,而應受傳聞法則之規範。故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委託鑑定所出具之鑑定書面,除符合檢察機關概括選任鑑定人之案件,或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五之適用外,概無證據能力,但參酌外國立法例(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四項),尚非不得使該鑑定書面之製作者在審判庭受詰問或訊問,具結陳述該鑑定書面係據實製作,亦即賦予被告就證據適格有反對詰問之機會,再據以判明是否承認其證據能力,以補立法之不足。
八、緩起訴處分
無效緩起訴
最高法院94年台非字第215號判例要旨:刑事訴訟法為配合由職權主義調整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乃採行起訴猶豫制度,於同法增訂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許由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之案件,得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為適當者,予以緩起訴處分,期間為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以觀察犯罪行為人有無施以刑法所定刑事處罰之必要,為介於起訴及微罪職權不起訴間之緩衝制度設計。其具體效力依同法第二百六十條規定,於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同條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即學理上所稱之實質確定力。足見在緩起訴期間內,尚無實質確定力可言。且依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於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仍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為由,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本於同一法理,在緩起訴期間內,倘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認已不宜緩起訴,又無同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所列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者,自得就同一案件逕行起訴,原緩起訴處分並因此失其效力。復因與同法第二百六十條所定應受實質確定力拘束情形不同,當無所謂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可言。
無效撤銷緩起訴
最高法院96年度台非字第232號判決: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如有違背上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之規定時,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緩起訴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分別定有明文。按緩起訴與不起訴,皆係檢察官終結偵查所為處分,檢察官得就已偵查終結之原緩起訴案件,繼續偵查或起訴,應以原緩起訴處分係經合法撤銷者為前提,此乃法理上所當然。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若係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者,苟被告已遵命履行,但檢察官誤認其未遵命履行,而依職權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並提起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時,該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之處分,即存有明顯之重大瑕疵,依司法院釋字第一四○號解釋之同一法理,應認此重大違背法令之撤銷緩起訴處分為無效,與原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無異。其後所提起之公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應視其原緩起訴期間已否屆滿,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或第四款為不受理之判決,始為適法。亦即,如原緩起訴期間尚未屆滿,因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係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以原緩起訴處分已經合法撤銷為前提之規定,應認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之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於原緩起訴期間已屆滿,應認其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違反「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依同法第三百零三條第四款之規定,諭知判決不受理。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183號判決:緩起訴係檢察官終結偵查所為之處分。就緩起訴確定之案件,如欲繼續偵查或起訴,應以該緩起訴處分經合法撤銷為前提。而緩起訴與緩刑之撤銷,同樣嚴重影響被告權益。緩刑之撤銷,依刑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二款、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二、三款規定,均以被告所犯他罪經判刑確定為要件;其目的在確認原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緩起訴處分之撤銷,雖僅規定於緩起訴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為之,未明定被告更犯之罪經判刑確定為要件。然查,我國緩起訴制度係為使司法資源有效運用,填補被害人之損害、有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再社會化及犯罪之特別預防等目的,參考外國立法例,配合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起訴猶豫制度。倘上開更犯之罪,嗣經判決無罪確定,表示被告無違反犯罪特別預防目的之情事,如拘泥於該款得撤銷緩起訴處分之文字規定,而認撤銷為合法,顯不符公平正義,無足以保障被告權益。基此,本院認為該款得撤銷緩起訴處分規定,宜為目的性限縮解釋。即被告更犯之罪,嗣經判刑確定,該撤銷固屬合法,但若經判決無罪確定,表示該撤銷自始存有重大瑕疵,係屬違誤。依司法院釋字第一四O號解釋之同一法理,應認該撤銷緩起訴處分自始無效,與緩起訴處分未經撤銷無異。則法院對該緩起訴處分案件,所提起之公訴,應視起訴時該緩起訴處分期間已否屆滿,而分別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三條第一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或同條第四款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而違背同法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再行起訴,分別諭知不受理。
九、準備程序
例外期前訊問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5185號判例要旨: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預料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而受命法官得於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時訊問證人之例外情形,其所稱「預料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場」之原因,須有一定之客觀事實,可認其於審判期日不能到場並不違背證人義務,例如因疾病即將住院手術治療,或行將出國,短期內無法返國,或路途遙遠,因故交通恐將阻絕,或其他特殊事故,於審判期日到場確有困難者,方足當之。必以此從嚴之限制,始符合集中審理制度之立法本旨,不得僅以證人空泛陳稱:「審判期日不能到場」,甚或由受命法官逕行泛詞諭知「預料該證人不能於審判期日到庭」,即行訊問或詰問證人程序,為實質之證據調查。
受命法官得為證據能力有無之調查
證據能力有爭執時,受命法官得傳喚相關證人到庭進行交互詰問。
證據能力有無由合議庭判斷
十、通信使用者資料的調取
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65號判決:關於通信使用者資料部分,雖然表面上只對檢察官有所規定,而未規定司法警察官在取得通信記錄時之法定程序,但檢察官在我國刑事偵查法制上,為唯一之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官依其層級僅分別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或受檢察官之指揮,偵查犯罪(刑事訴訟法第229、230條參照),依照法律之體系解釋,實在難以認為協助或接受指揮之司法警察官可以不受審查、自主取得人民之通信使用者資料,但作為偵查主體之檢察官卻反而要受法官保留及令狀原則之拘束。所以應認為司法警察官也應該比照檢察官受到同一限制,才符合我國刑事偵查法制之架構。(三)如果僅憑法律無明文對司法警察官限制,就認為司法警察官可以不受審查、自主取得人民之通信使用者資料,那麼檢察官就可以藉由指揮司法警察官之職權,指揮司法警察局不受審查地取得通信使用者資料。如此一來,上述法律規定對於檢察官偵查手段之程序限制,就形同完全被架空。這樣的解釋,應該明顯是違反立法者之立法原意。
李榮耕老師認為:
應修正通保法第11條之1第2項,使司法警察官得經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調取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然而,在法律修正前,司法警察官應可類推適用通保法第11條之1第2項,經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
違法調取通信使用者資料的法律效果:依刑訴法第158條之4權衡判斷。
